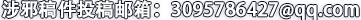11年的蜕变:从邪教徒转变为反邪教专家
1986年,刚离开邪教组织时,拉利奇写了一首诗表达她对邪教组织的憎恨:
其实我只是想要一个更好的世界,想为之而奋斗努力,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们却带走了我的灵魂,驱使我干一些违背意愿的事情,把我变成没有思想的东西。
最糟糕的是,
他们控制着我的一切——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财产和我的挚爱。
他们驱使我干一些违背意愿的事情,把我变成没有思想的东西。
我快疯了,无法控制自己,失去了自我,无法自拔。
更糟糕的是,
我替邪教组织工作,也对别人做了同样的事情,控制着他人的思想,把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东西,驱使他们干一些违背意愿的事情。控制他们如同我被控制。
拉利奇回忆说,“在邪教组织的那段时光,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很多场景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我完全与社会孤立,待在那个封闭、戒备森严的组织里。”
一个邪教通常由权威的个人领导,其他人只需顺从地遵循组织作出的规定。邪教的存在基本上都是以服务领导者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丰富和支持其成员的生活。
“我经常会对自己说,忘记这段经历吧,这件事不值得回忆。”拉利奇说,“最初使得我对这个组织的观念发生转变,是因为我母亲。我母亲当时得了脑肿瘤。邪教组织阻止我看望母亲,但是我违背邪教组织的意愿,借钱飞往密尔沃基为母亲治病。他们每天都会打电话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六周过去了,邪教组织最终说服拉利奇带着她奄奄一息的母亲飞回了旧金山。但是一回来,拉利奇就被要求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凌晨1点。“一天,当我回家时,我发现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拉利奇回忆说,当时我很伤心,只是愣愣地看着我和母亲的合影。
邪教组织又不让她参加母亲的葬礼。她违背了其命令,当她从母亲葬礼回来时,非常害怕组织会惩罚她。后来,她还继续在这个邪教组织待了两年。拉利奇解释道,“这就像一个女人遭遇了不幸的婚姻一样,脆弱的我过分地依赖着这个组织,仍然还对其充满着幻想和期望。”
最后,1985年,狄克逊出国。这个组织就解散了。
拉利奇离开组织后,她不确定她是否要重返学术界。她发现她有一种重获自由,获得新生的感觉。这感觉真是太好了。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重新找回了自信,找回了那个真正的自己。
拉利奇习惯了她在邪教组织中名字——“艾玛”。平时生活中,拉利奇一听到请愿也比较敏感,因为邪教组织以前总是在政府门口请愿。面对请愿,她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想知道谁在请愿,背后真正的推手是谁?
她后来搬到了纽约,找到了一份出版行业的工作,只能说她当时只是勉强地适应了外界的生活。“我每天都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看奥斯卡颁奖这样的节目也能看哭。一件很平常的事儿,自己也能伤感一阵子。”拉利奇说。
随着她自己慢慢地恢复了平静,拉利奇决定搬回加州,继续读完她的研究生。“其实当时并没有计划从事邪教领域方面的研究,接下来的生活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拉利奇感慨道,“我最初以为,今后的生活一定会远离‘邪教’。”
1997年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一发生,基于公众的反应、追随者的疯狂行为,拉利奇这才下定决心要开始从事邪教领域方面的研究。
“我想更深刻地了解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人加入邪教组织。”拉利奇说道,“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向大众普及邪教知识,防止误入邪途。”拉利奇下了很大决心才做了这个决定,其实这意味着再次在她伤口上撒盐。
从1997年到现在,通过多年研究,拉利奇教授已经出版了很多书籍。最近出版的《挽救你的生命:从邪恶和虐待关系中逃出来》。这本书被前邪教成员及其朋友和家庭广泛使用,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加入邪教的危害及其后果,以及如何辨别邪教。她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是基于她对1997年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和十多年来对邪教的研究。并且和玛格丽特·辛格博士共事多年,共同撰写了两本书:《我们身边的邪教》和《疯狂疗法: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什么》。
拉利奇教授还参与过审判美籍塔利班战俘约翰·沃克·林德案件和伊丽莎白·斯玛特绑架案。据了解,一位叫做约翰·沃克·林德的美国人,他是一名伊斯兰教信徒。他认为“塔利班是世界唯一的真正实行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从而效力塔利班政权,和塔利班战士一起抵抗美军。另外在伊丽莎白·斯玛特绑架案中,十四岁的伊丽莎白在一个富裕的盐湖城街区父母的家中睡觉时,被绑匪持刀绑架。绑匪大卫·米切尔自称为“先知”,他在妻子的帮助下,劫走了小伊丽莎白当作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他们不停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伊丽莎白一直被折磨了九个月才找机会逃走。
美国家庭基金会(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的前身ICSA)的执行董事迈克尔·朗戈尼认为,拉利奇教授书中认为邪教组织对其成员来说是“有限的选择”,这样的定义非常准确。
“目前,邪教方面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拉利奇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迈克尔·朗戈尼说,拉利奇教授的书籍浅显易懂,她非常机智,用异乎寻常,讲故事的方式阐述邪教方面的问题。
国际膜拜团体研究会还专门在亚特兰大研讨拉利奇教授的著作《有限选择》。
这本书包含她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博士毕业论文。这本书还解释了有限选择的理论,阐述了吉姆琼斯人民圣殿教琼斯镇集体自杀惨案和天堂之门集体自杀事件,并研究两个惨案的相似点,进一步探究邪教犯罪行为学和心理学。
人民圣殿教琼斯集体自杀报道:1978年11月,总部位于美国南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头目吉姆·琼斯(Jim Jones)将近千名追随者召集在一起。吉姆·琼斯告诉他的追随者,当局政府将进入到他们的农场,他们将受到伤害,遭受折磨,面临分离。他的解决方案是,在政府来临之前,所有人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将氰化物和安定混合在一起,强迫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意的人喝下。孩子们也被自己的母亲哄骗着喝下跟果汁混合在一起的毒液。
最后,包括276名儿童在内的917人喝下氰化物,倒在了地上。吉姆·琼斯也死于当天,但他并不是像追随者们一样死于氰化物,而是开枪自尽。政府当局到达现场,看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景象:一片尸体的海洋,人们一个挨着一个堆积在地上,旁边散落着空的塑料杯。
“天堂之门”集体自杀报道:1997年3月26日下午3:30,美国圣地亚哥市的警长接到一个匿名的报警电话,报告说圣地亚哥市富裕的圣菲兰奇镇(Santa Fe Ranch)附近一所房子里发生了一起集体自杀事件;后来警方查明匿名人叫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别名里奥·德·安吉洛(Rio DiAngelo)。两名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39具身着相同服装的尸体:有的性别难辨;验尸结果显示每人都喝了含有巴比妥盐酸的伏特加酒,这是一种致命的混合物;死者脸上都蒙着能令人窒息的塑料袋;有些男性还被阉割了;从自杀者们遗留在现场的录像带里的声明得知,他们都是一个叫做“天堂门”(Heaven’s Gate)的异教组织成员,自杀的动机是留下尘世的“躯壳”(肉体),以便灵魂登上尾随海尔-博普彗星的宇宙飞船。
在邪教组织中,他们的领导者通常拥有操纵性的、狡猾和迷人的性格。邪教组织的追随者都是一些普通,有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的人,这些邪教信徒被邪教组织控制着思想。拉利奇教授说,“实质上这种超意识形态并不是宗教。而邪教信徒们却坚信这种超意识形态,甚至这种超意识形态能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操控他们的思想,最后这种超意识形态就会最终形成一套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
拉利奇教授的理论研究超越了“洗脑”这样的流行语,她主要专注于研究是什么原因驱使人们进入邪教组织。
“这种思想的渗透,真是一个循循渐进的过程。”拉利奇教授介绍道,“我想了解,是什么原因驱使一些非常理智的人,去做了不理智的事情。”
“我认为,有限的选择就是关注这类人在特定环境下发生的变化。”拉利奇教授介绍道,“这并不是他们自由意志被剥夺了,而是他们的选择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受到了限制。”
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他们以为自己是“真正的信徒”。其实是他们的选择被邪教组织限制着。
关键是邪教本身用虚假的承诺来吸引人们,通过各种心理战术来控制他们。此外,他们利用宗教使许多人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些邪教头目,一旦这个信念建立,则很难动摇。那些孤独的、抑郁的、迷茫的和在痛苦生活中寻求答案的人们在邪教的这种控制环境下就更加依赖和敏感了。
“教会给了我一个团队和归属感,我感到骄傲,觉得生命有了意义。”——乔丹·维切斯(Jordan Vilchez),琼斯镇集体自杀悲剧中的幸存者。
有些人可能更容易被锁定在邪教环境里,他们认为教会给予他们的信仰和承诺能让他们得到自己正在寻找的答案。同样,归属感和共识度在人类精神层面的作用不应该被低估,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拉利奇教授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课题,最终也会引出一系列法律问题。如果邪教信徒不是被动的受害者,那他们是不是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个人责任是最棘手的问题。”拉利奇教授说,“社会该如何对待邪教信徒和他们行为?我并不是说这些邪教信徒有免除对他们行为负责的权利。”
拉利奇教授也希望公众能更进一步了解邪教组织的环境状况,以至于不会说出一些不合情理的话,比如有的人会说,“伊丽莎白·斯玛特怎么不早点逃走呀。”
拉利奇教授认为她的书会受到一些学术专家和心理学专家的衷爱,因为他们对书中伊丽莎白·斯玛特和派翠西亚·赫斯特绑架等案件感兴趣。
目前,拉利奇教授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下一本书籍的写作,这本书是关于在邪教组织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故事。 2001年,拉利奇被聘为加州州立大学的兼职讲师,现任教授。她被授予教授的专题课程为“社会学”,“魅惑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从事教学工作和研究社会学的博士生安娜·洛尼(Anna Looney)表示,《有限选择》这本书非常受业界欢迎。“拉利奇教授填补了邪教问题理论上的空白。她在学术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克拉克·戴维斯(Clark Davis)认为拉利奇教授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是位充满激情的教师,其专长已经超越了反邪教领域,她还擅长家庭结构和社会化问题。拉利奇教授在学术领域实至名归。
“作为导师,拉利奇教授总是教导学生,要批判性地思考问题。”克拉克·戴维斯介绍道,“拉利奇教授在邪教和邪教行为领域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国际认可。因此国际上不断寻求她的专家意见,并且学术期刊,报纸,文章和其他媒体经常引用她的文章和书籍。我很荣幸和她成为同事。”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呀!拉利奇的邪教信徒经历,反而为她有趣和充实的事业敞开了大门。
“这段邪教信教徒的亲身经历让我对邪教更有洞察力和透视度,为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拉利奇教授笑着说: “我当然也学了很多反邪教方面的专业知识。相比较以前,我更愿意以这种方式学习。”
拉利奇教授表示:“能把不愉快的经历,转变成积极的东西感觉真好。”
洛尼认为,无论从智力还是从韧性来说,拉利奇都是一个“疯狂”的人。洛尼说:“拉利奇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学者。” “激励她的事情之一就是想表达邪教信徒与邪教组织这种关系的复杂性。
洛尼说:“我对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表示同情。不过希望这些人都能像拉利奇教授一样,以另外一种更有益的方式来看待自身邪教信徒的经历,或许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邪教组织。”
拉利奇教授非常乐观和幽默。拉利奇教授有时就想,如果她没有走上邪教的道路,她的生活将会如何?
“我其实之前一直想成为一名小说家。”拉利奇教授说道,“要是按照最初梦想而努力,我肯定就在文学界圈子里面,或者在大学教英语。”
“我在邪教组织中待了11年。”拉利奇教授说,“11年里,我失去了我的至亲,失去了我的朋友。”
有时,她会轻描淡写地说,“我错过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繁盛期。”人们都会谈论起《全家福》这个喜剧片,还有一部影片叫做《总统班底》,那时大家都争相租这几个影片看。而我却一无所知。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就是空白的。
但是,拉利奇教授又是很幸运,没有像她同事兼挚友辛格博士一样,经常受到邪教组织的威胁和恐吓,她仅仅只是被起诉了两次而已。“我只是会偶尔收到一些邪教信徒泄恨的邮件。”拉利奇说,“我没有成为很多邪教组织攻击的目标,希望这样的状态能持续下去。”
事实上,拉利奇教授每次都非常谨慎,绝不轻易标榜任何特定组织为邪教组织。首先她不想轻易做出这样的判断,其次她是不希望她的判断导致最后判决出现失误。拉利奇教授说,“我研究的目的不是确定哪些是邪教组织。而是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邪教组织的模式,从而避免误入歧途,受到伤害。”
她鼓励人们用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自己去判断研究他们所在的组织。她接到了很多电话和邮件,有邪教信徒的家人寻求帮助的,甚至还有询问他们是否应该加入某个组织等。
“人们参与到这些组织的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我们也不可能只使用一个领域或者一种思维模式来解释这个复杂问题,而且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过程又与这些组织中的人有关。”拉利奇教授介绍道,“这不是宗教问题。这是建立在哲学或者信仰之上的权力结构和社会体系问题。”
拉利奇介绍道,“其实我只是想提出另一种看待这类群体和这些经历的方式。”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邪教信徒那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不堪回首。“我想,如果我不把这段经历充分利用起来,写入我的书中,真的很可惜。”
拉利奇教授现在仍然和以前的一些邪教信徒联系着,“我很开心看到,我们都从邪教组织走出来了,而且现在都在做着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贾妮亚·拉利奇
贾妮亚·拉利奇是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拥有人类学学士学位和组织系统研究博士学位,2007年被学校授予专业成就奖。此外,她是影响和控制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主要研究邪教和极端组织,尤其擅长宗教团体、政治和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等方面。拉利奇教授还是教育学、心理学、媒体和法律界的专家顾问。
拉利奇教授是美国社会学协会、宗教社会学协会、宗教科学研究学会和太平洋社会学协会的会员。她是国际文化研究协会的执行顾问,并在其杂志编辑委员会从事宗教研究工作。 拉利奇教授参加过很多国家和地方的电视和广播新闻节目,例如BBC、 Meet the Press、 NPR’s Morning Edition 等。同时她是很多邪教类纪录片和邪教类节目的顾问。